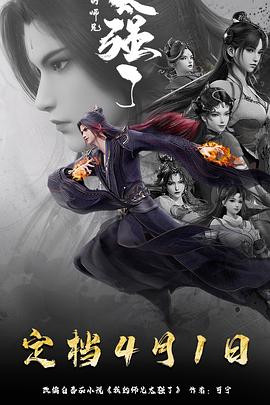资讯分类
《南京照相馆》 | 历史的罪孽要如何清算?
来源:人气:112更新:2025-08-05 23:30:02

《南京照相馆》
《南京照相馆》豆瓣评分8.6,成为今年暑期档最热门的电影。日军随军摄影师伊藤秀夫,为了冲洗彰显军威的照片,找到南京吉祥照相馆,市民因为洗照片逃过一劫。在冲洗过程中,日军泯灭人性的恶行逐渐彰显:杀人、强奸、掠夺……血腥残忍的场面在电影中被直观呈现,使观众感受到了强烈的心灵震撼。
对手无寸铁平民进行的屠杀,是侵略战争中最不容辩驳的罪行。然而,战后对屠杀罪行进行罪责确认,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影片中,无日军内部出于维护天皇荣誉、以“忠义”来包装美化自己的行为,将屠杀辩称为是对不识恩惠的人的惩罚;在战后法庭上,战犯拒绝承认屠杀行为,辩称如果不是中国军队很快弃城,民众怎会遭此灾祸?如果不是几位南京市民以姓名保住的那些相片,我们很难想象,参与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是否就因缺乏证据而逃脱了罪责?
历史上,不仅是亚洲,欧洲大陆对纳粹罪行的审判,同样是一场庞大的“贯彻正义”的社会实验,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审判,全面展现了追寻正义的过程为何如此艰难。
什么人是受害者?哪些人应当受罚?什么样的判罚是合适的?都是处在模糊地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标准的答案。
玛丽·弗尔布鲁克所著的《大清算》全面展示了这场持续数十年的纳粹审判暧昧、 含混的一面,打破了“二战”后德国彻底清算纳粹罪行的神话。在这场审判中,“正义”成为了一个颇具弹性的概念,各战胜国在不同阶段、不同对象上施予的“正义”并不相同,一些罪孽深重的人被轻松放过,一些人得到了远超其过错的惩罚。这场意在“贯彻正义”的审判,最终演变成了掺杂着政治纠葛、利益交换的复杂博弈。
难以贯彻的正义
1963年至1965年,法兰克福开庭审理了关于奥斯维辛的审判,它已然成为西德试图“应对和面对历史”的象征。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奥斯维辛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在审判过程中揭露的罪行恐怖程度所致。它还因为审判发起者的特定目标就是把整个大规模灭绝的系统送上法庭,而不是仅仅审判几个个体。
就公众对纳粹大规模灭绝政策的意识而言,法兰克福奥斯维辛首批审判显然是一个转折点。这些案件引起了媒体的热切关注和舆论的激烈辩论,并且使得人们的观点趋于两极分化,它在非犹太学者和普通读者当中确立了纳粹大屠杀的重要地位。
然而从司法清算的角度来说,奥斯维辛审判却不能代表人们以司法形式直面纳粹历史时所取得的成功,反而更能说明,任何此类行为都固有着某种短缺之处。
首先,这场审判证明,要在法庭上对大规模谋杀作出判决,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当一个集体暴力系统由国家启动并支持,吸纳普通人参与进来的时候,要以个体罪责的司法类别(而且雪上加霜的是,西德的司法体系还强调“卑劣的动机”或者“无度的”残暴)对其进行审判,必然会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情。

《纽伦堡:纳粹战犯在审判》
将奥斯维辛送上审判席的任务是浩大且艰巨的。在奥斯维辛的整个运作时期,共有约8200名男性党卫队队员和约200名女性守卫在这里工作过。这些人当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曾在西德受审,余下的7000多人从来没有被送上过法庭。
法兰克福奥斯维辛首批审判的检察官对被告进行了挑选,选出了那些他们觉得最有可能定罪的人选。这意味着审判对被告的选择不仅要考虑到他们在集中营系统中所担任的不同职业角色和工作场所,他们还要挑选容易被揪出来也能够展现出行凶者之残忍和虐待的人选。
审判的被告在德国被称作“作案人”(Täter),然而他们看待自己所作的“案”(Tat)时,却认为自己不具有个人能动性,也不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无论是在审判前的调查中,还是在审判的过程中,被告都声称他们与恶行的真实场所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对实际发生的事情并不真的知情,他们并不对杀戮负有任何责任,他们只是在遵从命令,如果胆敢不服从,他们就会给自己招致可怕的命运。
在法兰克福审判的审理过程中,许多证人遭到了非常具有进攻性的对待,采取这种行为方式的人士当中尤以辩护律师汉斯·拉特恩泽尔为代表。在早期的战后审判中(包括意大利的凯塞林案,以及几桩纽伦堡后续审判案),他就已经因为替纳粹分子辩护而积攒了名气。
朗拜因记录下拉特恩泽尔在奥斯维辛审判中是如何恶劣地对待证人,他常常因为证人无法回忆起特定事件发生的准确日期和时间而语带讽刺地暗示证人都是骗子。而在辩护的阶段,拉特恩泽尔则持完全相反的策略,甚至试图像被告自我呈现的那样,将他们说成是“希特勒的受害者”。
1965年8月20日,随着审判长汉斯·霍夫迈耶(HansHofmeyer)发表完长篇演说,宣布判决之合理合法,法兰克福奥斯维辛首批审判也宣告结束。由于此时的西德已经废除了死刑,所以最终判决中也就不包含死刑判决的选项。

《摩尔的审判》
在20名被告中,只有6人被判终身监禁;有10人的入狱刑期在3.5年到14年不等;有一名被告在奥斯维辛时期尚未成年,因此以未成年人的相关规定进行判罚;还有3人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
在审判走向终点的时候,西比尔·贝德福德告诉我们:“那位使尽全力让现场保持冷静,引领着法庭度过数次情绪的喷发和激烈的争吵,自己却从未情绪失控的法官霍夫迈耶博士,现在终于找到余裕的时间,陷入了崩溃之中。”
如果以将行凶者绳之以法为标准来衡量,这样的结果无疑是令人失望的。以被告犯下的罪行程度来衡量,许多判决都显得无足轻重,更何况为了使奥斯维辛得以运作,总共需要6000到8000名人员,而在法庭上被判有罪的仅有17人。鲍尔确实成功地让奥斯维辛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但是结果离他所追寻的正义相去甚远。
除此以外,在他为之努力的过程中,他也越发清楚地体会到这项事业的反对力量是如何盘桓不去:就像他对同事说的那样,每次当他离开办公室,他都感到自己仿佛生活在“敌人的领土上”。
补偿的不公
如果说惩罚有罪之人只是司法这枚硬币的一面的话,那么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和赔偿则是硬币的另一面。当受害者提出补偿的诉求却遭到拒绝时,或者当各个级别的补偿金额都低到侮辱人的程度,而曾经支持过希特勒的公务员、法官和医疗专业人士,以及曾经在军队或党卫队中服役,并且在战后继续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却能够得到很高的工资并且最终拿到全额养老金时,不公正的感触就会显得呼之欲出。
毫无疑问的是,无论什么样的举措都不能“弥补”纳粹政权的罪过,也不能让遇害的数百万人起死回生。幸存下来的人所争取的赔偿虽然同他们的受难不可同日而语,却仍然面临重重的障碍。那些被官方委任分发补偿金的人,可能自己就与前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

《安娜的战争》
此外还存在进一步的不平等形式,而个中缘由可能是有些幸存者群体可以通过有效的组织引起官方的注意力,也可能是挥之不去的偏见和同情心理,又或者是政治语境,以及不断变化的舆论风向。各地的情况详情有所不同,但是在第三帝国的继承国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给纳粹迫害和虐待的全部受害者提供全方位的补偿。
在民主德国,官方将国家社会主义阐释为“法西斯主义”,而曾经作为纳粹的左翼政敌承受痛苦意味着共产主义政府不愿意承认国家对“补偿”负有任何意义上的责任。苏联(它在同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损失了超过2500万公民)的首要关切是获得战争赔款来重建自身被战争摧残的经济,而为达成这一目的,它还在战争结束以后从东德抽调了材料、装备和人员。
尽管原因完全不同,但是奥地利也很明确地不愿为受害者提供赔偿。各个阵营的政党以及大多数国民都试图构建一种全新的“奥地利”民族身份,而这种身份将与他们所谓不情不愿地被纳入大德意志帝国的往事拉开距离,且不受其玷污。后继政府与公民社会都拒绝承认自己负有补偿或赔偿纳粹受害者的责任。
由于纳粹主义的“罪行”在法理上被局限为集中营守卫的虐待行为,“行凶者”的定义也受到了相应的限制,故而有资格要求赔偿的潜在受害者总人数也受到了限制。

《铁蹄下的村庄》
正如汉斯·弗兰肯塔尔所回忆的那样,尽管他的和弟弟恩斯特(Ernst)都曾在I.G.法尔本丁钠橡胶工厂做过奴隶劳工,但是他们总共只“收到了10,000马克的赔偿金,补偿企业曾将我们当作奴隶劳工,补偿当局曾将我们遣送,补偿我们失去的青春、在集中营里的监禁、失去所有的亲人,以及持续终身的身体和心理问题”。
某些社会群体所遭受的歧视不曾中断,特别是被视为“反社会人士”或“罪犯”的群体。反吉卜赛政策在战后德国仍旧生效,而许多官员本身就是曾在第三帝国时期“处理”过罗姆人和辛提人的纳粹官员。
比方说,在西德的巴登—符腾堡州,当受害人以被囚集中营期间受到不公正待遇为理由,提出赔偿诉求时,官方在1950年2月作出答复,“上述群体所遭受的迫害和囚禁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基于种族,而更多的是由于他们反社会和犯罪的态度”。
这番惊人的话语无疑有助于我们确认,纳粹党人即便没有证据证明“吉卜赛人”犯有任何特定的违法行为,也认为他们在本质上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具有“犯罪”行为倾向的观点延续到了战后时期。
用微小的赔偿摆脱责任
东西两德在1990年重归统一,然而这一过程并没有促使双方就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类相关事宜签订任何官方和平条约,故而来自各方的压力也就因此水涨船高。在热衷于审判案件和官司的美国就有许多板块开始对德国施加压力。
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曾经使用强制劳动力和奴隶劳工的德国企业(如西门子、大众汽车等知名企业)所面对的市场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如果它们拒绝承认自己具有污点的过去,如果它们拒绝抽出一部分利润为这些财富所倚仗的人们支付赔偿,那么它们的国际声誉将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弗利克·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德意志银行和大众汽车都越发被推向严厉的聚光灯下。
这一回,当局依然只在代表受害者的组织的强大压力下才作出让步。1998年,美国人对活跃于北美市场的德国公司发起集体诉讼。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愈发全球化的世界里,这些公司在德国国内也越发受到媒体宣传的挞伐;由于这些舆论有可能给销售和市场份额带来不利影响,它们也就势必要作出回应。

《三块广告牌》
这些公司作出了巨大的调整,这不仅仅是因为来自国际舞台的压力日益增大,也因为德国国内的运动越发声势浩大;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外部压力,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公司的政策调整是否会在目标的达成和实现上取得同等程度的成功。
德国企业的妥协方案将政府也牵涉了进来,它成功地将两大目标合为一体:一方面显然是一种在道德上负责任的立场,另一方面则是对德国工业利益始终如一的支持。在1999年到2000年期间,一家名唤“铭记、责任和未来”(EVZ,Erinnerung,VerantwortungundZukunft)的基金会在德国政府和个体企业的资助下成立了。美国和德国政府通过这一基金会就补偿金达成协议。只有满足了特定的条件,基金会才会诚恳地进行赔付。
这些条件包括(与近半个世纪以前的诺贝特·沃尔海姆诉I.G.法尔本集团案如出一辙),以后所有的诉讼案件都将搁置,个人诉讼也从此不予立案。除此以外,EVZ还在自身的融资背景上采取了一种非常狡黠的策略。
它关注的不仅仅是确实曾与纳粹勾结的公司,它还呼吁所有德国产业来支持这场以道德责任为根基的事业。超过五分之三的EVZ资金来自12家成立之初就在列的企业,而在总数多达6500家的成员企业中,约有四分之一的企业资助的金额低于1000马克——这实际上是一种表达道义支持的象征性款项。
德国政府和德国产业就是依靠这种方式,联合开发出一套关于责任的说辞。然而,还是没有任何人以公开或个人的方式承认自己身上担负法律的责任。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政府占据着道德的高地,而犯有重大罪行的行凶者却不用背负任何实际的罪责,就能轻松地隐身在一道徒有其表的责任之幕背后。
向人数已经变得相对稀少的在世幸存者给出象征性的赔偿,这件事情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再次巩固了德国能够面对过去的道德声誉,但是它并没有以一种相对精准和有的放矢的方式解决罪责的问题。进展当然不可否认,但即便是深度参与赔偿的获取,以及协助建立“铭记、责任和未来”基金会的人也都承认,这一迟来的正义并不全面完整。

《我们的父辈》
关于痛苦、磨难和不公正的档案记录似乎永远都翻不完。所有那些没有白费的司法调查,所有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幸存者的痛苦证言,以及所有那些由被调查者及其亲友提供的口供,现在似乎都很难有益于司法正义的事业,而只能为历史学者所用了。
如果有罪之人基本上都能逃脱惩罚,那么只有无辜的人会受苦,而且将继续受苦。除此以外,就算他们等到出席法庭的那一天,那也未必是一个可以真正供他们讲述经历的舞台。
无论如何,清算过去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故事,审判在其中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人们解决罪责问题的大部分精力并没有耗费在法庭的公共舞台之上,而是用在了家中相对私密的空间里,用在了家人、朋友和邻里之间的讨论中,或者用在了回忆录和日记的个人记述中。
比起法庭上的对抗,反而有更多人卷入了这些私密场合的清算中。而且,每个人与过去的私下较量,并不像法庭判决那样清晰和一锤定音,而是一个缺乏明确目标,始终变动不居的过程。
最新资讯
- • 暑期档国漫再出佳作,《浪浪山小妖怪》满意度86.9分居年度第四
- • 影史最惨 “反向宣发”:这些电影还没上映,就被现实按在地上摩擦
- • 终于等来这神级丧尸片续作
- • 《731》即将上映,日本人什么反应
- • 电影《731》背后的历史真相!一桩肮脏的秘密交易!
- • 借《浪浪山的小妖怪》,聊聊奇幻影片里的角色身份问题
- • 照片的背后,是不能遗忘的历史!
- • 电影非常克制、非常冷静,大家可以放心去看
- • 《东极岛》《奇遇》《玛丽和麦克斯》……本周新片看哪部?
- • 苹果的影视狂飙?《F1:狂飙飞车》与沉浸现实电影的崛起
- • 《南京照相馆》 | 历史的罪孽要如何清算?
- • 《捕风追影》:新老交替的阵痛与复杂
- • 《浪浪山小妖怪》预测票房超9亿,无名小妖也有高光时刻
- • 暑期档票房单日破3.7亿 全国影院相关企业超9.2万家
- • 大鹏:债没还完,人破防了
- • 豆瓣8.7,这是公认中国最优秀的女性佳作!
- • 在动作片没落的时代,《捕风追影》却逆风翻盘,它都做对了什么?
- • 《浪浪山小妖怪》导演自曝彩蛋!确认致敬《黑神话》
- • 大佬们精神暗合!黑神话主创力挺国产新作《浪浪山》
- • 三观炸裂,这部法式电影太敢拍了!